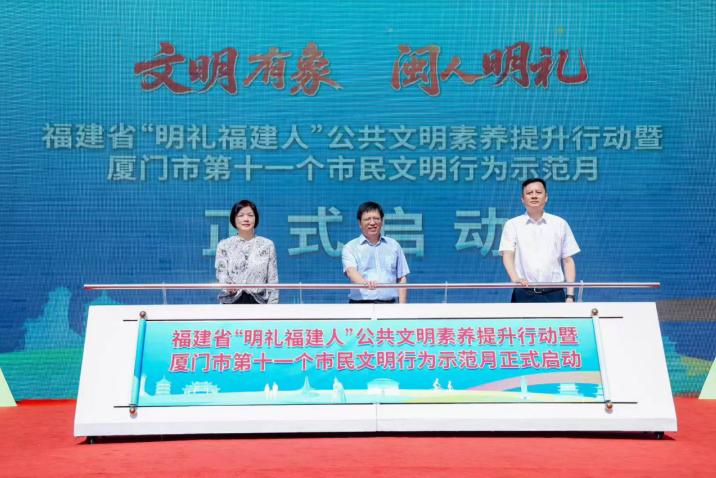【子曰文化】
作者:曹雅欣
国学走入生活,
传统成为时尚!
科普国学,
文化健康!
“子曰”,古代指孔子说,现泛指老师说。
“子曰诗云”,就是中国人引经据典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
子曰文化,团结一批杰出的国学教育者和文化工作者,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解读古为今用的经典智慧,构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把精英层面独有的思想智慧,转化为民族共享的文化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提出的第三个价值准则,是诚信。
诚于中,信于外,“诚信”这个词,要分“诚”与“信”两个方面来看。

(一)无信不立
信,是“诚信”最直观的行为表现和检验标准,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说话一定信守、做事一定办到,讲究信用,受人信任,这是诚信的外化体现。
“信”之一字,虽然千金一诺最为沉重,但空口无凭又最为虚泛,观其行径还要等待漫漫时间的印证,所以,“信”在外化体现方面,就产生了一种加固信任的仪式。仪式也并不复杂,中国的印章,就是这仪式化的凭信。对于一国来讲,国之玉玺,郑重一落,就印盖出了国家信誉;对于个人来讲,名章为凭,红印一盖,就代表着本人信誉。
所以理想化的“信”包括了三个维度:主体信诺,客体信任,而连接这主体与客体的,就是信誉。首先自己有诺必信,而后才能建立信誉,最后赢得旁人信任。
“信”对国家、对个人都极为重要,《左传》中就说,“信,国之宝也”,信用是国家的重宝。信誉建立,比城池建造、比经济建设都更难,建立之后的维持亦难,信诺百事可能才筑造起一道信任的高墙,但毁诺一事就可颠覆信任的根基。国之信,建之无形,毁之无影,易毁难建,去即无存。这个道理,两千六百年前的晋文公重耳就深深懂得。
重耳做公子时曾流亡楚国,为感谢楚成王对他的款待,便留下信言说,倘若将来他能回国而遭遇晋楚两国交战,一定让晋军退避九十里,以谢今日收留之情。这就是“退避三舍”这个成语的由来。后来,战况果如重耳所言,晋楚两军对决,晋军退避九十里后才战,最终赢得城濮之战的胜利。而在晋军后退的时候,军吏曾表示过强烈反对,认为国君躲避臣下十分耻辱,楚军又已是疲惫不堪,正好攻而破之。但重耳的舅舅子产,代替重耳发言说,如果没有楚国的前恩就没有晋国的今天,不能背弃恩惠而食言。此战之后,也成就了晋文公重耳一代春秋霸主的地位。成就他的,不仅是实力的响亮,更是人格的响亮;成就晋国的,不仅是国力的强大,更是国格的强大。这就是《孔子家语》里说的:“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国家一言之信,胜过万马千军。
一国对外要维护信用,对内也要建立信誉,面对国家民众才能形成政府公信力。《论语》中就记载有关于公信力的讨论,学生子贡曾向孔子询问治国之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充足粮食、充足兵力、人民能信任政府,这就是治理政事之要。但子贡总有进一步的思考,他继续问,在这三者理如果必须要去掉一项,能去掉哪一方面呢?孔子说,“去兵”。子贡还想探寻答案的唯一性,于是又问,如果再去掉一项,在粮食充足与人民信心里,能放弃哪一方面?然而这道艰难的选择题没有令孔子为难,孔子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的治国理念是,在迫不得已之下,粮备可以去掉,没有粮食,不过是死而已,但自古以来谁也免不了死亡。可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家就立不起来了。
因此,政府必须要能取信于民,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问政、论证;因此,宋代宰相王安石也从治国实际出发,言古论今地总结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政府传递给人民的信义力量重过百金,这就是中国思维中的政论、政见。
所以,国之信,重九鼎。对内,民无信不立,对外,国无信不威。

信,与个体每一个人的关联更为密切,我们平日里,一句邀约的问候语、一篇工作的保证书、一段信誓旦旦的承诺,都是在进行着某种信约的发起和践行,在这过程中,可能言者无心,然而信者有意。我们每一天的言行印证、每句话的结果论证、每个人的印象旁证,都是比印盖在契约上的人名章更有说服力、更有真实度、更具考验性的人生信义证明。
信,就是要对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也许有时候只是夸张的表达、只是随意的答应,可是语言之后没有行为的续接、没能圆满的完成,这段话就缺少了漂亮的收尾、这个人就缺少了完整的责任意识,言过其实,便成了言而无信的人。正如孔子感叹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如果不讲信义,简直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所以古人对自己出言十分谨慎,从战国时期的《春秋谷梁传》就态度鲜明地指出:“言而不信,何以为言!”如果不能守信,那何以要说话!到汉代的《大戴礼记》更同意这观点,说:“可言不信,宁无言也!”如果言而无信,那就宁可不说话!宋代程颐进而总结道:“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没有忠信之心的人,不可立世为人。这样看来,信,不是品格的高层次要求,而是人生的必要性条件。
故此,古人对“信”的教育和反思时刻警醒在心头。《韩诗外传》中就记载了“孟母不欺子”的一段故事。孟子小时候,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好奇地问为什么,他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杀猪?孟母心不在焉地随口打发他说:杀猪给你吃!但是话刚脱口而出,她就后悔了,想到孩子已有认知观念,怎么可以传输他“人无信义”的理念呢?于是,贫寒度日的孟母依然拿出钱来向邻家买了猪肉,只为给孟子传达“言出必行”的教育理念。孟子能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亚圣”,实在离不开母亲对他幼年的点滴教育。
育人如此,自育亦然。成年后的孔子,也是不忘随时对自我进行反思教育,他要求自己每天多次反省自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为人办事尽心了吗?与人相交诚信了吗?所学知识践习了吗?为事要忠、为人要信、为学要习,孔子最看重的人生品格里,信,就是关乎能否立身的重要一条。
信是一种品格,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信是一种责任,一言九鼎,一诺千金。
信,更是一种准则,人无信不可,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威。

(二)无诚不行
信,是一种行为验证,然而“诚信”这个词,“诚”在“信”前,“诚”比“信”更为重要,诚,是内心自觉。诚信,必须心意真诚,才好信守约定。
所以孔子论诚信,为我们所熟知的那句“言必信,行必果”之后加了一句令人惊愕的话:“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出言就必须要信守、做事就必须要坚决,这并非君子所为,而是没有判断能力、不问是非黑白、浅薄固执己见的小人行径!这句话真是石破天惊!言行一致并不一定代表诚信品格?——在孔子这句话里,就涉及到了“诚”的重要性:假如被迫做出的承诺不是本心所愿,假如一时糊涂的约定不是正义所为,那么还要去义无反顾地践行它吗?假如对坏人做出了违心承诺、假如做坏事顺从了错误约定,这些权宜之计、这番歪理邪说反倒要如约信守吗?当然不是!只有正义才值得信守,只有诚恳才甘愿信诺——内心的愿意,才是守约的根本!
对孔子这句惊人论断,从小受诚信教育长大成人的孟子就深以为然,孔子说了小人的言行,孟子便明确说君子的言行。《孟子》中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内心通达的君子,所言不一定拘泥信守、所行不一定执迷结果,为人行事的准则,是必须要合乎正义。“惟义所在”,唯有正义存在,才能心正意诚。
所以宋人晁说之就说,“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人无信不可立,心不诚更不能行。不讲首要的诚心实意,仅凭“信”的结果来衡量人品未免会有失偏颇。没有心之诚在前,信之行就成了刻板的教条、拘泥的桎梏、僵化的思维、固执的行径、不情不愿的强迫、形式主义的空洞。而民国时期,修炼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之圆融大境界的弘一法师,便说道:“内不欺已,外不欺人。”不欺人,便是“信”,不欺已,便是“诚”,如此内外合一、表里如一,才是“诚信”的本质。
诚,这正是中国文化以浓墨重笔论述的重要内容。《大学》里论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孟子所言的正义、正心,都是从“意诚”开始。能秉真诚之性、能怀赤诚之心、能发坦诚之言,才能拥有正直的心、才能遵循正义的理、才能奉行正义的事。
而《中庸》又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才能明了真理,明了真理才算真正心诚。所以,在不明理时作出的错误承诺,本就是心不正、意不诚的,怎能再信其行、顺其非,让错误更加荒谬地履行?
“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贯穿了万事万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万物,因而君子以诚为贵。这也正是“中庸”这一智慧思想的重要出发点,中庸之道的做法就是:本于诚、用于中、致于和。
“诚”是君子最看重的本心,先做到“诚”,而后才能达到《孔子家语》里描述的理想状态:“言必诚信,行必忠正。”诚信这个词因而涵盖着内外两方面的意义:诚于中,信于外。
中庸之道要“本于诚”,诚信之道要“诚于中”,由此可见,诚之为贵,就在于它关乎着内心的本源,是为人为事的出发源点,若本末倒置,只要求表面行为的达标而忽略了对内心意愿的安顿,便是缘木求鱼,背离了“诚信”的本质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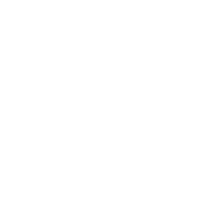
国之诚信,在固邦,在安民;
人之诚信,在立世,在明道。
荀子说,“养心莫善于诚”,那么,正行莫善于信。
诚信为人,就是在养自我清洁之心、正自身坦荡之行;
诚信对人,就是在养天地浩然之气、正道义永存之风。(文/曹雅欣 书法/张瑞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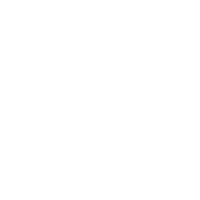

特别感谢:书法家张瑞龄先生
- 【2014-09-02 】· 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
- 【2014-09-02 】· 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
- 【2014-09-02 】· 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
- 【2014-09-02 】· 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
- 【2014-09-02 】· 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