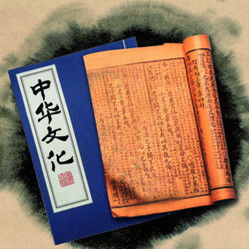
文学的生活化,是指文学创作不仅出于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是作为社会生活行为而存在,创作目的直接指向现实生活,而不是文学自身。中国文学的这一本质特征,不仅是中国文学自身规律形成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原动力。因而,把握中国文学的生活化本质,是摆脱20世纪西方近代文学观对中国文学研究造成的困境的关键所在。
从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文学也有审美追求,但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中国文学的作者,从来不曾认为文学是为审美、为文学的,而是更多地将文学当作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绝大多数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中国文学也因此形成了生活化的本质特征。这主要表现于下列几方面:
一、以文求官。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文求官的传统。战国策士游说君主,阐述政治、外交主张,以谋取职位。这游说之辞整理成文,便是《战国策》中的文章。当时也有不少策士并没有向君主面陈己见,而是通过书信对君主进行游说。如《秦策一》载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从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可以看出,苏秦游说基本上是以上书的形式进行。汉代自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见知于汉武帝,作赋以求仕进便屡见不鲜。六朝受士族情趣的影响,历代帝王都喜爱文学,故献诗、献赋以求仕进亦不在少数。如鲍照献诗刘义庆,“寻擢为国侍郎,甚见知赏,迁秣陵令”。于是,“学而优则仕”遂演变为“写而优则仕”。
自隋朝开始,科举制度通过诗文选拔官员,由此产生了士人以诗文备考的行为。如白居易《策林序》说自己为应举,曾和元稹等在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唐代之后,这种备考行为更为普遍。《金史·选举一》载:“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全元杂剧》载无名氏《张公艺九世同居》云张狂、李奈应举,贡官云:“你来应举,会吟诗么?”张狂云:“会吟诗,会课赋。”可见元代以诗文会课也是普遍现象。清代,这种为应举而平时以诗文会课的状况依然不改。如《曾国藩文集·家教篇》说,家中“男近与同年会课作赋,每日看书如常,饮食起居如故”。
 |
 |
责任编辑:康金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