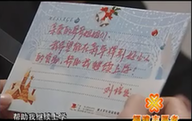3
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铁生都不仅活出了自己的尊严,也活出了文学的尊严,而在这些尊严的背后,是他的出自内里又深怀虔诚的敬畏之心,敬畏生活,敬畏生命,敬畏文学,敬畏读者。
对于生活,他更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本身,如他曾说道:“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不要抱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不必抱怨生命中有太多的曲折。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的翻滚,就会失去雄浑,沙漠如果失去了飞沙的狂舞,就会失去壮观,人生如果仅去求得两点一线的一帆风顺,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
而对于写作,他是在生活的衍生与延伸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把握的,他说:“写作是一种可能性的生活。”在你生活的日常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其实这种可能性,经常是在夜里自己的梦中实现。也许不能说是“实现”,算是“虚现”吧。最好的形容是梦,梦想。在你的梦想里出现的一些可能的东西,它在现实中不能成立或无法达到,而写作可以帮助你达到。”因为重视写作与生活的内在勾连,文学与心灵的密切互动,他又强调指出“你是不是给自己的心灵写。这是首先要问的问题。”因此他这样告诉人们:“每一个朝阳的升起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不论多么困难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这些年来的文稿整理出来结集出版。”时间的弥足珍贵,使他从不懈怠自己;生命的弥足珍贵,使他从不慢待文学,文学的弥足珍贵,使他从不轻待读者。
铁生说他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然而就是这个利用“病隙”写作的业余作家,在异常艰难的生存境况之下,从七十年代后期起,连续写作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小说佳作与散文精品,如《午餐半小时》、《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老屋手记》,《我与地坛》等,从80年代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当代作家之中,史铁生不是最为有名的,也不是最为畅销的,但他以他的内敛式语言传扬着真挚而达观的人生理念,用他的哲理化的感悟释放着真切而浓郁的人间温情,与读者最为贴心,与大地最为亲近。
 |
 |
责任编辑:邓宇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