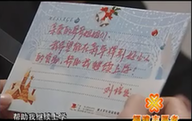2
回想起铁生的人与文,以及与他有关的人与事,有两个关键词渐渐地凸显出来,总在心头萦绕,这就是“豁达”与“尊严”。我觉得如果要概述他留给我的印象,这两个关键词要更为突出,至少可以表达目前我对铁生为人为文的主要感受。我甚至认为,铁生所以是铁生,豁达与尊严这两个精神品质,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其基本内核。铁生以此成就了自己,也以此启迪着我们。
豁达之于铁生,是两个意义上的。一个是为人,一个是为文。
我们知道,铁生因为罹患尿毒症,长期以来要靠透析维持生命。而他的尿毒症系由肾病发展而来。而越来越严重的肾病,则源于插队劳动期间得患的腿病,因耽搁了最佳治疗时间,最终导致了双腿瘫痪。说实话,他是最有资格抱怨的,也最有理由诅咒的,从青春历程的人为中断,到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乃至个人命运的明显不公……但是,他既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在默默承受这一切中,尽力扩展自己的承受力,有意锻磨自己的忍耐力,用越来越宽广的胸襟,越来越博大的心志,在精神的层面上,去化解一切磨难,掌控自己的命运。当有人对他总要依赖透析表示同情时,他却说道:“幸亏有透析,要是倒退20年,这个病就是绝症,就没有办法。在近五六年,透析技术才比较成熟,所以我还能有这个状态。”他这样独到地去理解残疾:“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在送给朋友陈村的书上,他干脆写道:“看来,残疾有可能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他如此达观地去看待命运:“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上帝在每个人的欲望前都设置了永恒的距离,公平的给每个人以局限。”“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这些用苦痛和心血换取来的真知灼见,首先开导着他自己,然后又启迪着我们,使人们更通透地理解人生和更宏观地把握命运。
就为文而言,铁生给人的印象是,在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创作拓进与文学演变中,似乎处处有他,又似乎处处无他。
1979年,他用《午餐半小时》一作,加入当时的“伤痕文学”的大合唱,但却以说实话、讲真话的方式,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随后,他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等,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但却以抒写知青与农人之间的深挚情感而使作品别具一种乡间情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由《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和《中篇1或短篇4》等中篇小说,表现出借鉴现代派手法和趋于先锋性写作的大胆实验;同时,他又以《好运设计》、《我与地坛》等散文名作,率先在散文写作中追求思想含量与文化意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杂糅的方式,在人性审视与人生探悉上呈现出全新的风景,也达到少见的高度。他的散文《病隙碎笔》,更以纪实与联想、反思与断想的连缀,构成当代散文随笔写作新的艺术高峰。可以说,所有的写作倾向与文学思潮中,都能见到他的独特声影,但他又不止步于某一类文学写作,从而专属某一个文学流派。由于洒脱,因而超脱;又因为不断突破和始终参与,他成为了三十年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贯穿性作家。
 |
 |
责任编辑:邓宇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