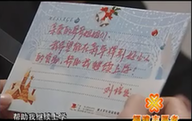1
我与史铁生,相识得比较早,交往也比较多。“文革”后期,他从北京到延川下乡插队,我在黄陵本地回乡务农,同属于延安地区的知青一代,因此感觉上有种莫名的亲近。他因病回京之后,我也从西安调至了北京。他在雍和宫大街26号的平房的家,在水锥东里28号楼房的家,或与友人同往,或自己单去,都曾去过多次。后来我在当时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编辑出版过他的《我与地坛》和《史铁生作品集》(3卷本)。对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从早期的短篇小说,中期的散文随笔,到后期的长篇小说,因为既是读者,又是编者,也比较了解和熟悉。他于2010年12月31日突发脑溢血逝世后,对于他的人与文,我一直都在回味与梳理,但越想越觉着怎么也理不清,说不尽。
因为他纯粹又丰沛,深刻又高远,许多不同的因素集合于一身,很难简单地予以解读。
在2011年1月4日于北京“798”艺术社区举行的“铁生与我们同行”的追思会上,看着墙上贴着的铁生的照片,人们手里持着的铁生的著作,我在心里不断地向铁生说道:“大哥,你好!大哥,走好!”确实,铁生对于我,就是“大哥”一个,而且最恰切不过。他年长我一岁多,按年龄说,就是大哥。更让人为之敬重的,还是他的胸怀,他的识见,他的广博,他的厚道。朋友们有什么事,总爱找他唠叨唠叨,听听他的意见。朋友间有什么不同看法争持不下,谁说这个问题铁生说过什么什么,大家立刻停止争论,集体表示认同。他在或不在,他好像都是朋友们的主心骨。你无论谈论什么,无论人生与人性,还是文学与文化,抑或是宗教与哲学,他都似乎是有备而来,与你娓娓而谈,而且不乏精彩之见。
我常常暗自感叹,他阅读的书怎么那么多?他知道的东西怎么那么广?他思想的问题怎么那么深?而以他的残疾之身躯,这一切都堪为奇迹。而因为他为文写作的不拘一格,为人处事的达观随和,人们常常会忽略和忘记他是一个残疾人士,都把他当成是可交心的文友、可纫佩的作家,并在情感上和精神上,把他当作可亲近的大哥,可钦敬的兄长。
 |
 |
责任编辑:邓宇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