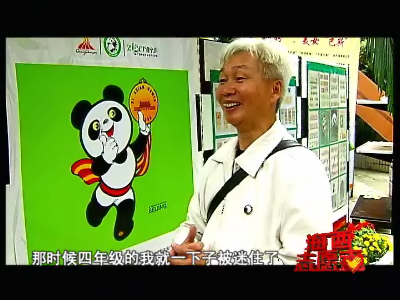国际关系十年
这十年,中国是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多样化最大受益者。中国的崛起包容着不同的要素,包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政府主导与经济至上、历史传统与先进文化……它承载着太多太多的矛盾,还要去突破思维的僵化与体制的瓶颈,试图成功使得自己“软着陆”。
矛盾的时代,纠结的中国
中国正在走的,或即将走的是无人走过的,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主义,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抗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它是把截然不同的两个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结合在一起的“第三条路”。
文/加藤嘉一
一
“加藤,你当时是为什么选择去中国的?”
这个问题,我至少被问过上千次。一开始没能很清楚地给予答案,刚来中国的2003年4月,我才18岁,边想边说,花一至两小时才能让对方明白我选择来中国的背景与理由。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被问与回答的不断重演,此刻,我终于能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解释清楚了。这意味着进步还是退步,我不知道,让时代去说吧。
日本人从幼年时代就开始吸收中国古代的历史、思想和人物,对“中华”两字抱着崇拜之心。我们的社会尊崇“以和为贵”和“天人合一”,还有最重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汉字则是百姓生活和交流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
我这个以与众不同作为人生准则的另类少年,从小向外看,每天瞭望世界地图,想象国际关系的理想国。因对内的保守与封闭不满,渴望能出去,并从海外的视角观察日本社会。只是想确认日本社会极端排斥个性,盲目保护共性的“维稳”方式是否是国际通用的,况且,最好能去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国家,这样才能对比得更鲜明。
读高三时邻居中国的首都——北京申奥成功,我一直在课堂内外对世界历史和国际问题感兴趣,所以狂学了英语,高二开始当翻译,那时抱着将来去联合国工作的愿望。英文掌握得还可以了,为了去联合国,还需要增加一门,阿拉伯语和俄语算了,感觉合不来,法语太优雅,不适合我,西班牙语明显不够严肃,我是一个不会跳舞的无聊男人,就熟悉而陌生的汉语吧。我有个弟弟和妹妹,家庭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长子去欧美国家留学,就只能奔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低的国家。
主观与客观,乐观与悲观,主动与被动,期望与不安,积极与无奈……都有。但综合来看,我的出国战略似乎是最终自然而然地落脚到中国身上。这叫缘分,换句话来说,是命运。我幸亏获得了公派身份,运气良好,老天没有忘记我,本人就遵从了上帝的安排。从本科到硕士,享受到了6年的全额奖学金。2003年到2010年,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一切都是没有想到,出乎意料的。
1999年8月,我15岁第一次出国,毕业旅行,到悉尼奥运前夕的澳大利亚呆了两个礼拜。那次外游让我开阔了眼界,并论证了一个事实:不是我在日本体验的事情彻底符合国际惯例和标准,世界原来充满多样性,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到外国走一走,接触不同的文明体系,将能够让自己加强对谋生的信心和希望。从澳洲回国后,我下决心,上大学时一定出国。
2001年7月,中国北京申奥成功。我17岁,作为亚洲人,更是东亚人,我也感到很高兴,为北京感到骄傲。它意味着,中国北京就像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东京一样,将进入迈向奥运主办国的黄金时段。坦率说,之前我对中国的认识更多来自“悠久历史”和“华夷秩序”,不过是神秘的乌托邦而已。而北京申奥成功把我和中国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很多,在我眼中,它逐步变成现代的,现实的,现成的存在。确信,若北京没走那条路,我不会选择来这里。
2003年4月,我终于来到北京。当时还没有第三航站楼,那是在举国体制下为奥运建造的象征品,同时带着实际用处,就像中国造航母的战略。我坐东航着陆二号航站楼,从机场走出来,对北京产生的第一印象就是“黄”,不是所谓“扫黄”意义上的,而是来自国际上著名的沙尘暴之黄。空气很不好,令人陷入黄昏状态。我上正规、红色的夏利出租车,起步价与今天一样10元,每公里比现在的2元便宜,1.2元。师傅把肚子暴露出来,很像是个啤酒肚,白色的袜子,穿着黑色的皮鞋(什么个时尚感呢……),在抽烟,身上有浓厚的味道,应该是10多天没洗澡了。我很抱歉地说,我对北京或中国的第一印象只能用“糟糕”两字来形容。
我在北大宿舍第一位同屋是巴勒斯坦人,据说是阿拉法特的亲戚。我是带着“三无状态”来到北京的——没有人民币,没有中国朋友,不会中国话,我跟他只能用英文交流。他的房间太乱,空间太小,我根本没法住下来,换了房间,第二个同屋是蒙古驻华大使的儿子。
我原来有个担心——来华后生活彻底变成中国化,英文怎么办,不能丢的,必须想方设法去维持水平。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北大留学生宿舍“勺园”简直是“小联合国”,来自100个以上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抱着“同一个梦想”共存着,英文往往是我们之间交流的通用语。我把中文和英文同时提高起来,创造了相辅相成,一举两得的局面,这是我在华留学的意外收获。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我们外国留学生的最大动机和目的为:好好了解中国,学好中文,扩大人脉。这是“低投入—高回报”的合理化投资。我后来在勺园建立的外国人脉简直是难以置信,为将来的有关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所谓“第三世界”——非洲、东南亚、拉美和中东等地区的留学生。他们多数是驻华大使女儿、首相儿子等牛人,实际上是来华潜伏,进行游说的。看看当今中国对这些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展开的经济外交、能源外交、文化外交,全都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第三世界的政府也以派出优秀留学生的方式搞好与中国的关系,为未来的国家建设铺垫。
2006年11月,在北京隆重举行的“中非论坛”文艺晚会上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刘芳菲一起主持的是我在勺园的邻居,也是我来华后第一个朋友,来自非洲贝宁的留学生吉尤姆。此人的中文,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的了解是本人根本无法去超越的。我预测,吉尤姆将来一定在中非之间扮演重要角色,最起码大使,正常发挥外相,有可能当国家一把手。刘芳菲在自己央视博客“我的搭档”上这样写:“许许多多像吉尤姆这样的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关于非洲最生动,最鲜活的信息。因为有他们的往来穿梭,那块大陆上的人对我们也感觉不那么陌生。但这些友好的使者却要承受着孤单和思乡之苦。给周围的非洲朋友们一点温暖吧,因为我们是朋友。”
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哈佛、斯坦福、耶鲁、牛津、剑桥、东京、早稻田等来自发达国家大学的许许多多的学生也来北大了解中国,学习中文,其中肯定也有与它搞好关系的投资意向。在国际关系学院读本科的4年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新加坡留学生。他们基本都跟我一样是公派学生,与我不同的是,他们是属于高中毕业后就跟国家签合约,确定北大毕业后回到祖国哪个单位的超精英分子,商务部、外交部、旅游局、《联合早报》等。新加坡这个面积不到北京海淀区的都市国家把向中国派出留学生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前总理李光耀曾说过一句颇有哲理的话:“东亚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和日本同时强大的局面,古代是中国强,日本弱;近代以来是日本强,中国弱。而此刻,东亚正在迎来‘两强’时代,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两个强国之间,新加坡将采取务实、灵活、独特的国家战略,拭目以待。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学生也是如此。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来华留学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享受外国生活,学习语言的范畴,实际上,稍微夸张地说,全都是为了祖国未来的对华外交谋取相应的人脉和应有的情报——潜伏。我经常被中国人称为“日本有关部门派来的间谍”。我当然否定我是以交换或运输所谓情报的方式谋取金钱和权力的间谍。不过,对于中国本身来说,来华的人用什么方式谋生并不重要,只要来到中国,尤其是当今世界的权力中心——北京的人,都会产生感受、观察和思考,带着这些“礼物”回国,向有关部门汇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难道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不这样做吗?百闻不如一见,我们看到的都是中国真实现状和本来面貌,而不是商业化的媒体粗心报道的中国。这一交易的过程当然对中国造成压力,理所当然,我们也在付出成本,承担风险。
肯定的是,既然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无法选择把国家彻底封闭起来,甚至只能不断以开放、自由、民主的方式展开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国家方略,那么,中国要告别盲目担心或排斥外国优秀人员的弱国心态了。既然你有强国梦,就要有强国心。“可怕的中国通”太多了,我这个小小人物算什么东西,请你们睁开眼睛。
做大国哪有那么容易呢?中国政府和民众需要做好心理准备,要明白“祖国高度、密集、广泛被关注”是怎么回事,什么逻辑。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人员、金钱、信息等要素多米诺式地流入到中国,形成热潮,他们都是谋求“低投入—高回报”的自私品。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2007年12月,我陪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来北大演讲。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高官、著名学者、媒体人、商人等纷纷来到北大,北大有关部门没有一天是不接待的,天天忙于“高校外交”。他们是以拍马屁的方式进行游说,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和赞扬。这一切对中国来说顶多是压力,中国人根本没有时间和余地对此感到骄傲,自以为“牛逼”。
2008年5月,我在北大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主席过几天正好要访问日本,我祝福他历史性访日圆满成功。我在中国也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官员、商人、媒体人、学者等各界人士。令人感恩的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向我这个7年前什么也不是的,从事言论工作的日本80后赋予了特权和宽容。他们甚至主动跟我接触,以传送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告诉我什么是中国,中国人是谁,中国需要什么,什么是中国利益。我能感觉到,有些长辈真的发自内心地支持我、鼓励和安慰我,他们认为,把未来走向政坛的加藤嘉一培养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我很欣赏他们的主动、激情和关怀。我一定证明你们的投资是合理而正确的。我已经把中文表达与写作看作一辈子的事业和任务了,同时也一定用我的母语以及其他会运用的语言,把真实的中国传达给世界,让中国人更多了解世界,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请大家相信我,我做过的,正在做的,即将做的事情一定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也更加自信地向世界表达一种情感:我做过的,正在做的,即将做的事情一定符合国际社会的核心利益。
国际社会如何面对崛起中的中国,中国如何与国际社会打交道。这是21世纪初期的世界政治要解决的最大课题。它走向何方?我无法确定。但坚定不移,毫无动摇的前景是,中国与世界,或世界与中国已经形成“命运共同体”了。如果甲方崩溃,乙方必然崩溃,反之亦然。
 |
 |
责任编辑:徐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