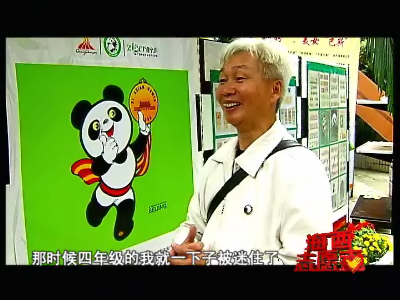公安部再次重申:不得歧视、辱骂、殴打,不得用游街示众、公开曝光等侮辱人格尊严方式羞辱卖淫女。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刘绍武:“以前叫卖淫女,现在可以叫失足妇女。特殊人群也需要尊重。”
评论一:捍卫权利比改名“失足妇女”更重要
眼下已是初冬,扫黄的声势依然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不过,扫黄者为了展示其公正与宽仁的一面,决定对扫黄的对象予以“正名”——自然,不是将卖淫产业化、合法化,而是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刘绍武在公安部工作会议上称:“以前叫卖淫女,现在可以叫失足妇女。”据说这是为了表示对特殊人群的“尊重”。
更名就是尊重?卖淫女的称谓有多么低贱?“失足妇女”就很中听吗?
且说“卖淫”之名。查古汉语辞典,有“卖客”、“卖笑”,却未找到“卖淫”;“卖淫女”更无踪迹可觅,流行的称谓是“娼”、“妓”、“花娘”、“校书”等。“卖淫”是一个现代性词汇。“淫”字确含道德贬义,但是换成“卖身”、“卖肉”,效果一样糟糕。若袭用古称,说“卖笑”,似乎雅致了些,却令某些买客不知所谓。思来想去,在“卖”字之下,恐怕很难找出更合适的词替换“淫”字以精确描述这一职业。
而且,“卖淫”之名所含有的道德贬义,十分契合意识形态建构。政治典章与法权纷纷收纳了“卖淫”。中文版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刊有:“早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出现了与强制女奴隶献身于男性现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法文皆称“卖淫”。前者对应经济道德化,后者对应法律道德化。
如今,终于意识到了“卖淫”一说的道德贬义过于浓烈,打算换一个冠冕堂皇的称谓。然而,这不是亡羊补牢,而是头疼医脚。再说用来替换卖淫女的“失足妇女”。“失足”难道不具贬义吗?且所谓“妇”者,指已婚女子。即使将涵义扩大化,妇女当指18岁以上的女子。18岁以下称少女,14岁以下称幼女,7岁以下称儿童。如果卖淫女不足18岁(西南某地不是出过身为小学生的雏妓吗),还能叫“失足妇女”吗?所以,这一轮替换,实为不妥。
这么说并非为“卖淫”之名辩护。我只是想指出,如严复所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词语的生产,如大浪淘沙,最终淘出的那一颗熠熠发光的沙砾,流行多年,自然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如果说它不雅,首先是因其所指物不雅。要改造,当改造此物。是故,与其争论用什么称谓以替代卖淫女,还不如在打黑扫黄的同时,依法捍卫“失足妇女”的权利:不得歧视、辱骂、殴打;不得挂牌游街示众;不得曝光她们备受摧残的姓氏与容颜;更不得在派出所里对其凌辱、强暴。这后一面的工作能多做一分,卖淫女就多得了一分尊重,减轻了一分耻辱。这种尊重,乃是出于对人权的看护。(羽戈 作者系青年学者)
 |
 |
责任编辑:徐嵘 |